当前位置: 广州刑事律师网 > 刑法罪名 > 私分国有资产罪 >
国企改制过程中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之界
国企改制过程中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之界分
发布日期: 2012-03-04 发布:
2007年第12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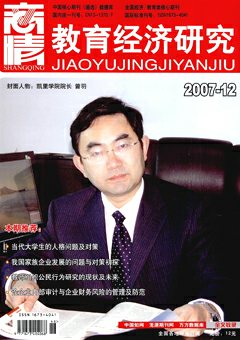
[摘要] 当前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隐瞒资产真实情况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的犯罪行为之定性仍是实践中的一个难题,尤其是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之认定,常存在分歧。本文从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这三个方面对这二罪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进行分析,以求对实践中此类犯罪活动的明确定性有所助益。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 国有企业改制 贪污罪 私分国有资产罪
目前,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隐瞒资产真实情况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的情况比比皆是,许多此类的犯罪层出不穷,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刑法的规制,成为最后保护国有资产在企业改制中不受损害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就目前情况看,有关此类损害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仍旧是各地检法机关不易辨清的一个难题。以一案例为证:
浙江省某市燃料公司为一国有企业,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于1998年实行企业转型。在资产评估过程中,公司经理徐某明知公司的应付款账户中有三笔共计47万余元系上几年虚设的情况下,未向公评估人做出说明,隐瞒了该款项的真实情况,从而使评估人员将三笔款项作为应付款评估并予以确认。公司党支部书记罗某从徐某处得知公司资产评估中存在虚报负债的情况。在公司改制过程中,部分职工知道这一内情后要求对上述虚增的47万余元进行私分,于是徐某与罗某商定召开职工大会,经讨论并确定虚报负债部分用于充减企业亏损或上交国有企业管理部门,但实际并未按此方案处理。2000年6月30日,处于改制过程中的燃料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长为徐某,副董事长为罗某。同年12月,该市某区人民政府路政部门发出文件同意燃料公司在21名职工中按购买款平均配股。尔后,徐、罗与应某等5人收购了其他16名股东的全部股份。自2000年4月份以来,罗某明知公司资产评估中存在虚报负债的情况,而未向有关部门报告并继续同徐某一起到有关部门办理企业改制后继手续。2000年9月7日,该燃料有限公司向所在区财政局交清燃料公司国有资产购买款465.3969万元。随后,徐某、罗某等人积极办理公司产权转移手续,直至案件。
关于此案之定性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徐、罗二人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理由是徐某作为燃料公司经理,在企业改制过程中,隐瞒公司的财会账册的应付款项中有几笔是公司虚设的真实情况,取得资产评估人员的确认;而罗某在得知资历产评估中存在虚报负债的情况下积极同徐某一起办理有关改制后续手续。二人之行为使原国有企业的47万余元转入到改制后的企业中。2000年6月30日该燃料有限公司首次股东大会明确新成立的公司的股东为原公司的全体21名职工,改制后21名职工平均持股。因这47万余元直接影响到改制后的企业总资产,也影响到这21名职工的实际利益。在股权均等的前提下,实质是原21名股东平均分配了47万余元国资款,两人仅仅各占二十一分之一。但两人作为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违反国家规定 ,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应对国有资产47万余元的私分负责,其行为应认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罪。另一种观点,亦即审理法院的判决认为,徐某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为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资产评估中,对公司虚设负债款不作说明,从而骗取评估人员的确认;罗某明确该公司在资产评估中存在着虚报负债的情况,而积极与徐某一起到有关部门办理企业改制后继手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二人之行为均应认定为贪污罪。
司法机关对该案的判决无疑是正确的。但笔者之意不在于仅仅讨论些上具体案例,而是借此例引出本文正题,证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此类犯罪问题的定性上的模糊性: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损害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中,常涉及的几个罪名有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妨害清算罪等等。其他罪名再所不论,笔者此处只就最易出现混淆的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进行分析,以求对此类案件的定性问题有所助益。
处理上述此类案件时,认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罪还是贪污罪之所以常出现分歧,是因为两罪确实存在诸多相似的表象,尤其是许多贪污犯罪的行为人为了掩盖自己侵吞国有资产的主观目的而将国有资产作不同范围的私分的情况下,对这二罪进行清晰的界定就更加困难。尽管二者存在诸多的相似这处,但是其本质还是不同的,因而在认定国企改制过程中的隐瞒资产的案件中,对私分国有资产罪和贪污罪进行区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主体方面
主体(行为人)的范围和数量不同。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罪名解释出台之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对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称谓中都带有“集体”二字:集体私分罪、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集体私分公款罪。可见,“集体”一词提示了私分国有资产罪复数行为主体的团体性或整体性,它能使人们对私分主体的范围大小及其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大体性的掌握。而贪污罪中主体的团体性或多数性并不是其必备的特征,但隐瞒国有资产过程中的贪污行为,恰恰多表现出多人或集体行为的特点,一般为以上级为主的上级与下级的共同贪污;或者是负有监管义务的上级未尽义务致使下级贪污的行为。这也是在实践中,对此类犯罪认定不一,易被混淆的一个原因这所在。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从主体的数量和范围这一点上对二罪加以斟别:首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强调的是单位的整体性,而共同贪污行为表现出的则是主体的多数性,而不在于是否为整个企业的行为。这也不是说,凡是企业内绝大多数人参与的即为私分国有资产罪,而少部分人实行的即为共同贪污犯罪。不能片面的单纯以人数多少来加以区分。其次,在同为多数主体的情况下,二罪主体的分工也是不同的:贪污犯罪行为的主体为多数时,各主体之间的行为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各环节之间是缺一不可的。而私分国有资产罪,犯罪的主体只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各主体之间往往形成一种合议,其牵连性不明显。当然也只能由这些人员承担刑事责任。
二、主观方面
1.策划者或参与者主观方面的目的不同,所谓主观目的是指决策者是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取利益还是为大多数人谋取利益。在私分国有资产罪中,决策者及参与者多是为企业内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行为,因而私分对象除了决策者外,还有单位内部的其他人,并且这“其他人”常常人数众多。例如:某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员用假发票报销,谋取公款,但为了平复个别职工的不平,抽出部分赃款给职工发奖金的案例。虽然从表现上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得赃对象的集体性的客观特征,但实际上仍是企业负责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扩大分赃的范围,故应仅追究负责人员的体育活动犯罪的刑事责任。
2.得赃者的主观方面是否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同。如上文所述,在贪污行为中也常常出现得赃者的范围大于决策者或参与者的情形,鉴于此类情形,可以从得赃者在主观上是否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来加以界分。若各得赃者对所得款物的来源、取得途径等均系明知,并且均存在占为私有的主观故意,则可认定谋取国资的行为人,即得赃者为共同贪污犯罪。但若得赃者中有部分人并不具有私占公产的故意,或者有些得赃者对所得款项的来龙去脉根本不清楚,只是被动的接受分配的话,则不可能构成贪污罪。而只能对存在故意的策划者追求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刑事责任。上例即可对此种情形加以说明。
三、客观方面
1.得赃者是否具有犯罪行为不同。此一区分标准是由上述“是否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延伸而来,故尔可与上述标准结合予以判断。在私分国有资产罪中,策划者之外的绝大多数得赃者,因为没有谋取私利的犯罪故意,故也没有实施隐瞒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而在贪污犯罪中,各个得赃者均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且行为表现出共同性,或者共同实施同一性质的行为,或者因职务的不同而具有各自不同的分工。
2.分得赃款的行为在企业内部的公开性不同。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行为一般在单位内部具有相对的公开性,因为其常是以“以单位名义”做出的,因此私分国资的行为不仅私分对象知道,私分对象范围之外的人往往也知道,只是由于自己不符合私分对象的条件而未能分到钱物。但贪污犯罪是绝对不公开的,行为的策划与实行都是秘密进行,绝不让策划分赃者之外的其他人得知。因而有学者也将“决定是否以单位名义做出”作为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和贪污犯罪的关键,其实也就是讨论二罪之行为的公开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媛媛,邱 红.《论贪污罪共犯中的几种形式》.辽宁工学院学报,2006,2.
[2]周其华.《贪污罪几个问题的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4.
[3]朱孝清.《国企改制中隐瞒国有资产案定性研究》.《人民检察》,2005.1(下).
[4]李寒芳.《私分国企该当何罪》.《产权》,2004.
[5]丁海勇.《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之异同》.《检察实践》,2004,4.
[6]张成法.《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比较研究》.《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快速投稿通道





